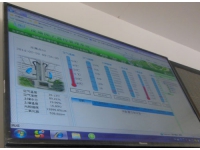本文对农业劳动力需要与剩余的考察,不是采用以上方法,而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这方法可以简述为:用社会劳动的总投入与总产出之比作标准来衡量农业劳动的投入与产出之比,即以社会劳动者总量与国民收入值之比作标准来衡量农业劳动者数量与农业净产值之比,由此得出农业劳动力的需要与剩余的相对量和绝对量。其主要理由是:
(一)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国民收入”是全社会劳动者在一年内所创造的价值的总和,马克思把它叫做“年价值产品”。一方面,它是社会劳动总投入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一年之内所推动的劳动的总和”。(《资本论》第2卷第428页)同样的道理,作为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的农业劳动,其投入 是农业劳动力,其产出是农业净产值,或者说,农业净产值体现了所推动的农业劳动的总和。
如此说来,“国民收入值/社会劳动者人数”的经济意义就是平均每个社会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量,其倒数“社会劳动者人数/国民收入值”则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即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社会平均生产力的作用,”(《资本论》第1卷第52页)起着衡量各个部门劳动的标尺作用。它要求“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衡量农业劳动,则在农业劳动中达到这个水平的部分是必
要的、被社会承认的,而超过这个标准的部分则是不必要的、剩余的。因此可以说,农产品价格符合其价值,则全部农业劳动都是社会需要的;而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则农业劳动中就只有一部分是必要的,而有一部分必是不被社会需要的,是剩余的。总之,“花费在单个商品上的劳动,只是作为属于它的和在观念上进行估价的总劳动的可除部分,才有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0页)对花费在全部农产品上的农业劳动也应该是这样。
(二)这种方法是把农业劳动作为同其他社会劳动同质的人类劳动,即对农业劳动从抽象劳动、一般劳动的角度考察。而正是这种同一的、同质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本身提供了计量计算的可能性。
(三)虽然非劳动时间也可能是生产时间,但只有劳动时间才创造价值,非劳动时间不创造价值。从抽象劳动角度来考察农业劳动,就可以把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严格区别开来,还可以消除由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农业劳动在一年之间分配上的不平衡带来的对农业劳动计算上的困难。
(四)因为社会劳动产品的总价值等于总价格,实际对农业劳动的考察通过对国民收入和农业净产值的运算来进行。这样,农业与非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农产品与非农业产品的价格水平都直接决定对农业劳动考察的结果。这样考察的农业劳动的需要与剩余就不只是与耕地面积、农机数量有关,不只是与农业生产内部的因素有关,而且也与农业外部的、整个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发生了联系。即是说,凡是影响劳动结构变动、影响农产品价格与非农业产品价格的因素,也就成
为影响农业劳动需要与剩余的相关因素。这样,许多原来难以定量考察的非经济因素,都可以转换为可以定量分析的价格因素、劳动力数量因素。这样从事物的总体上、从事物之间的各方面联系上去考察认识事物,就可以避免片面性。
(五)从抽象劳动角度考察农业劳动,因为有了社会必要劳动作标尺,可以根据现有的经济统计资料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每一年农业劳动的需要与剩余情况,从纵向的历史的考察中来发现农业劳动的变化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
这种新方法的采用,要求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自然经济下小生产者单个人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无需由社会统一计量也无法计量;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使抽象劳动为人们所理解,使社会对劳动的计量既有必要也有可能;联合劳动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则提供了科学计量劳动、按比例分配劳动的现实性。从我国目前看,广大农村只是处在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渡的阶段,人们对劳动的看法实际上难免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这也必然影响到人们对这种考察方法的理解和实际的运用。反过来,这种方法的运用将有助于冲淡看待劳动的自然经济色彩。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实际的价格体制常常是人为地使价格背离价值,目前对粮食仍维持两种价格,这里的种种非经济因素既然干预了经济活动,也必然使单纯经济的考察方法产生局限性。同样,单纯经济的考察方法也有助于揭示和排除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干扰作用。
三、三十年间农业劳动的考察和结果分析
单独观察1952-1982这三十年间我国“社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国民收入”、“农业净产值”这四栏统计数字,它们都是一直增加,难以看出规律性的东西。然而,若把这四个指标联系起来,使它们组成一个“农业劳动需要率—N值”来加以考察,马上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N值从1952年以来先是一直减小,由69%减到1978年的48%,达到最小值;自1979年开始迅速增大,于1982年达到62%。若以年份为横坐标,以百分数值为纵坐标对N值描点作图,则曲线相应地先下降后上升,1978年既是最低点,也是转折点。见下表:
1952——1982年间我国农业劳动需要率的变化
项目 年度 52 57 65 78 79 80 81 82
国民收入值(亿元) 589 908 1387 3010 3350 3688 3940 4247
农业净产值(亿元) 340 425 641 1065 1318 1467 1658 1893
社会劳动者(万人) 20729 23771 28940 39856 40581 41896 43280 44706
农业劳动者(万人) 17317 19810 23398 29426 29425 30211 31171 32013
社会劳均净产值(元/人) 284 382 484 755 826 880 910 950
农业劳均净产值(元/人) 196 220 274 362 448 486 532 591
农业劳动需要率N值(%) 69 58 57 48 54 55 58 6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
由N值的经济意义可知,自建国以来农业劳动就不完全是社会需要的,是一直有剩余的;其剩余程度在1978年以前有增无减,到1978年农业劳动剩余最严重;自1979年以后到1982年,农业劳动被社会承认的程度提高了,农业剩余劳动减少了,到1982年大概恢复到五十年代的水平。纵观整个三十年间,以1978年为转机,前后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N值,农业劳动需要率,农业劳均净产值占社会劳均国民收入的比率,是一个高度综合的社会经济指标。它既可以反映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各业的差距以及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又显示着社会经济宏观决策的优劣。结合实际情况看,我国五十年代迅猛发展重工业,对农产品实行低价的统购统销政策,限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的流动;六十年代,自然灾害、“大跃进”等造成初期三年的农产品奇缺及整个经济的困难;中期开始的“文化革命”动乱,延续到七十年代中期达十年之久,使得社会劳动结构凝固僵化,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决定了这个阶段N值曲线的低落;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首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力,继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农村广泛推行生产责任制,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及乡镇企业,使得N值在这个阶段迅速抬升。N值的小大变化及其曲线的降升转折,表明我国国民经济由比例失调不正常发展转变到比例比较协调的、健康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这即是N值及其变化所透露出来的主要信息。